張艷
向以鮮的散文集《兩朝詩影》,帶我們進入了公元7—13世紀的時刻。那個在中國文學史上耀眼的時代,前人已將詩心調度得或柔媚生姿,或鏗鏘悲愴,或深入骨髓。向以鮮用一根彩繩串起,以詩人、詩事、詩典為經緯,把千古佳作在中國文脈中留下的剪影、側影、倒影、掠影甚或幻影,編織出彩云朵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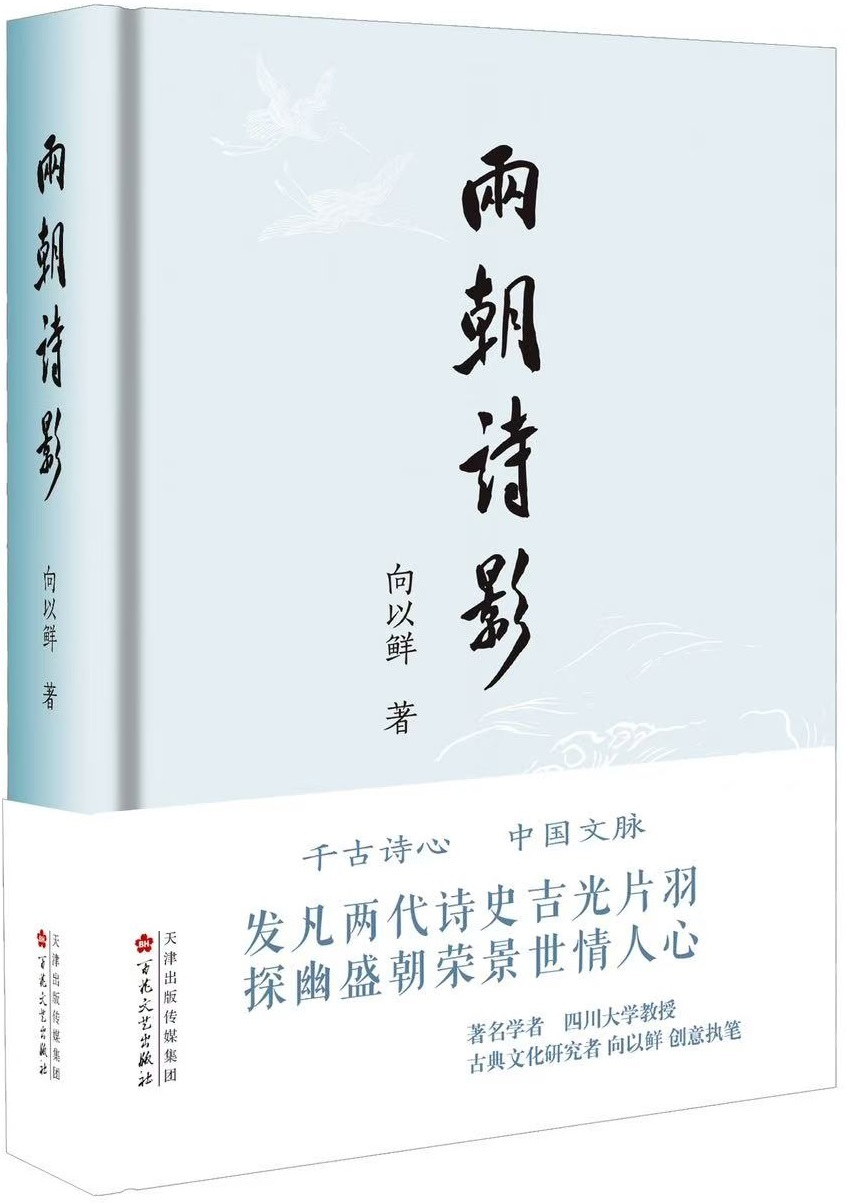
閱讀《兩朝詩影》,要有藝術、哲學、美學、歷史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儲備,還要具備辨析能力。讀《兩朝詩影》里引述的詩句,那悠遠的兩朝氣息,各路英雄們或輝煌或落寞的一生,從記憶中復活。
在《我家江水初發源》《春夢或西方》中,特意將蘇東坡織入篇章肌理,是作者字斟句酌的有心之舉。《春夢或西方》跳出單純的史料鋪陳,在歷史敘事與人文思考間尋得平衡,直抵生命哲學的深處。《我家江水初發源》僅幾千字,將東坡關鍵的幾年和最美的詞道盡,把東坡的精神氣質寫得透徹。
草堂雨夜,杜甫靜聽潤物雨聲,暢想曉來錦官城繁花帶露,揮就《春夜喜雨》。在《喜雨札譚》中,作者逐字釋析,甚至連“花重錦官城”之“重”的多音讀法都做了細究。即使這樣仍不盡意,引出清人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的見解:“雨驟風狂,亦足損物……曰‘潛’、曰‘細’,寫得脈脈綿綿,于造化發生之機,最為密切。”為這份共鳴添一筆佐證。
從40年前跟從導師系統學習唐宋文學,到古代典籍的校點與整理,再到教化育人的大學教授,在古典文學中沉浮醞釀幾十載,向以鮮感慨:“有歷史厚重感的文字能禁得住推敲。”
在后記中,他寫道,《兩朝詩影》以一事一物為切口,不止珠聯詩文麗影、璧合詩詞群英,重要的是,它以個個散點,透視唐宋文明的盛世榮景,更勾勒出存身其中的兩朝生民的生態與心念。
引述歷史材料做文章,作者的文字敘述不是被歷史牽著鼻子走,而是以輕盈的筆觸洗去歷史沉重與凝滯的一面,以不被理性桎梏且有著如夢幻般想象力的文字,與縱貫逾千年的代表性與特征性的文化銜接呼應,聯絡得恰到好處。
這樣的書寫方式拆解了時間與空間理應千萬的距離,帶有切膚溫情。語句片段,脈絡清晰,過渡自然,掌故鮮活,周折曲轉,在無限的可能性里,加入見解或猜測,把我們帶入無以言說的詩境,又把我們帶出唐宋兩朝時空。
李敬澤談到作家評論他的《青鳥故事集》有意義時說:“這肯定不是學術作品,我從未想過遵守任何學術規范。恰恰相反,它最終是一部幻想性作品。”這句話也是為《兩朝詩影》量身定做的注腳。李敬澤的意思其實是說,一個單純的學者,可寫不出這么好的東西來。
“古籍整理是一種十分傳統的坐冷板凳工作,如何平衡枯燥與詩意的天秤?又如何在發霉變黃的典籍中發現現代性詩意?其實,任何事物中都飽含詩意和現代性。孟子說得好,萬物皆備于我矣,反身而誠,樂莫大焉。詩意和現代性并不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,只存在于春花秋月、愛恨離愁、玄學思辨或后工業文明景觀中。不,不是這樣的,詩意和現代性的存在邊際遠遠超出我們的心力所能企及之地。我的很多作品,都是在翻閱古代典籍時寫出來的。”可以想象,作者翻動泛黃書頁,對典籍中那些藏在字縫間的細小動因,懷抱著近乎本能的敏感。
讀到《胡姬魅影》一章,我驟然一驚,原來這篇文字早在兩年前讀過,而且在我寫的《編輯手記:文字對著真與善》,還摘取了最后一段:“橫貫中西方文明的絲綢之路,不僅給中國的大唐帶來自由、開放和繁榮,也帶來了氣象萬千的異質文化。穿行其間的胡姬,如同穿花的蛺蝶或翠鳥,作為一種肉體之美的存在,為唐代詩歌舒展、幻化、催生出璀璨的、令人意醉神迷的萬千魅影。”
讓我們回到李白的《少年行》吧,那樣的韶光時代,那樣的得意揚揚,那樣的旁若無人,那樣的純粹和放縱:“五陵年少金市東,銀鞍白馬度春風。落花踏盡游何處?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
真的找不出比這句子更美的了。一部好小說,往往在結束的時候,又昭示著新的開始。詩影昭昭的散文集《兩朝詩影》亦是這般,那樣的韶光時代,那樣的純粹和本真,閃著真金白銀般的光。
(《兩朝詩影》,向以鮮著,百花文藝出版社,2025年12月)
【未經授權,嚴禁轉載!聯系電話028-86968276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